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门,北欧国度的公费医疗闻名全球。在丹麦,就诊和查抄均是免费,药物用度凭据累进制减免。而支撑这一福利的是,普通人交税的比例到达收入的一半以上。笔者得到的丹麦当局奖学金,每月也要交36%的税。
我曾问丹麦人,对如此奋发的税率有何观点。他们的答复是:他们相信,他们本日交税辅佐其他生病的人,当本身某天不幸生病时,也能得到辅佐。
这个别系既有漫长的期待又有高效的细节,既有暖和的处事又有酷寒的拒绝,既有富裕的信任又有偶然的迷惑,误诊、耽搁诊治也时有产生。而将这些悖论融合为一的,是全民健身的社会民俗,只管给人少添贫苦的社会自觉,老是选择信任的社会文化。
作为一个慢病患者,笔者本人在北欧的求医中经验过数次惊奇和愕然,也曾因一些温情时刻而打动,最终无奈地学会了耐性期待,少措辞和知天达命(或曰,接管现实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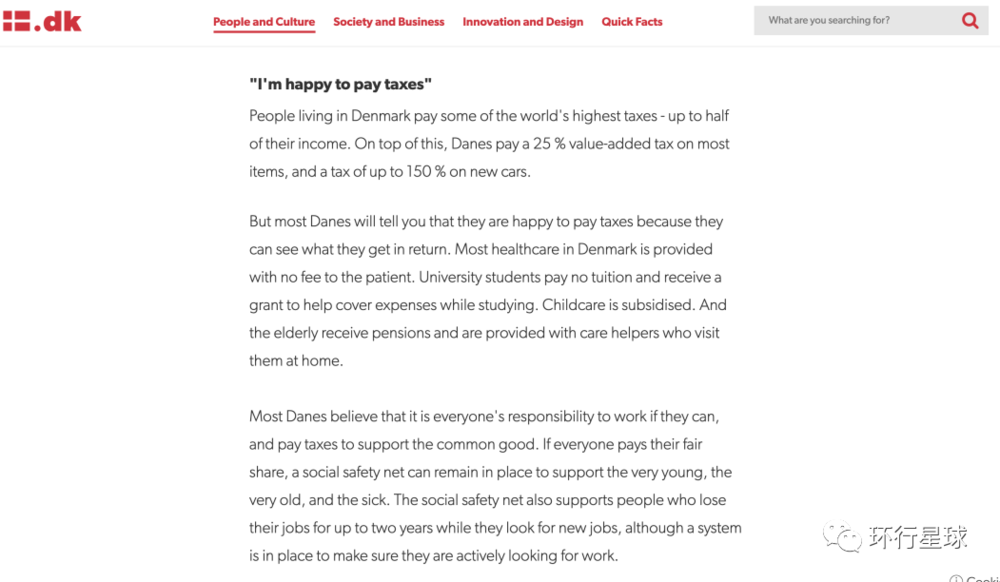
丹麦官网显示人们要缴纳的税高达他们收入的一半。对新车缴纳高达 150% 的税,但他们很乐意纳税,因为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图:denmark.dk
2017年刚到丹麦时,我跟GP(全科大夫)曾经因为一个难以定名的差别产生摩擦。我向她报告我已抱病三年,前因效果,如何服药,减药进程,等等。其时我是同时吃甲巯咪唑和优甲乐。有大夫会选择让病人只吃甲巯咪唑一种利便调药量,也有大夫担忧指标突升突降带来眼部症状而让同时吃这两种药,但无论在老家照旧北京的医院,无论大夫本人倾向哪种服法,大夫都一听就懂这些服法和背后的考量。
但在丹麦,GP听完后就问我,我不懂,你为什么同时吃两种药效相反的药?你这样吃是没用的。我试图和她表明这是一种在中国很普遍的服法,大夫的思量是只管和缓地调药制止眼部症状,制止药物性甲减,等等。她依然不解,生气地说假如你这样我不能医治你。
在分开后,其时的男伴侣说,你适才很是不尊重大夫!你怎么可以质疑她!我说,我只是在向她表明,中国的做法和丹麦纷歧样不代表中国大夫的做法就是错的啊;不代表我就没有原理啊。他说,可是在丹麦没有人会质疑大夫,所以你跟她争论在她看来就是不尊重她。最后的办理方案是,我换了一个GP(因为欠盛情思再见她,因为总以为在这个医患干系精采的气氛中我像个医闹),并改成只吃甲巯咪唑。
我无法总结导致这次摩擦的差别毕竟是什么。文化的?社会习惯的?这里是不是埋没着一种狂妄?一种日积月累出的狂妄?可能只是见识差别?这只是北欧给我的第一个文化攻击(cultural shock)。随后,公费医疗体系的各种不绝攻击着我——
由于各类事情的薪资程度都很高,大夫又相对辛苦,愿意学医的人并不多。医学生以一部门有情怀的人和一部门移民构成(收入很高的整容医师除外)。护士更是需要从东欧国度招募。大夫天天见的患者数量很少,履历相对有限。
一个例子是,我的GP在给我做心电图时,试了好屡次都没打出票据。他叫来护士,才发明没有按某个键。而他读心电图的要领,是用一把尺子量每个图形的长度,然后一一比拟(作为比拟,海内医院心电图仪器根基会自动陈诉心律不齐等问题)。
但当地人没有“百度查病”的习惯,他们无条件相信大夫。在这里,化验单和查抄陈诉都以电子版发送给大夫,若非主动查询或索要,患者甚至不会看到,自然也不会拿脱手机查询每项指标的意义(而我在海内常常这么做……)有位伴侣在传闻我有甲状腺问题后,汇报我她也有,而当我问是什么问题时,她却茫然不知;只汇报我大夫开了药她就吃。
北欧国度因为医疗资源有限,且是公费医疗,收治都有严格的转诊制度,而GP就是这个制度的第一个守门人。除急诊外,各类问题都是由GP先诊断,按照严重水平选择是否转诊到专科大夫或医院。譬喻,在伤风发热时,GP给的发起都是:喝柠檬汁、吃止痛片、发热高出一周不退,再去找他。
而当地人如觉是小病,也都自觉不去就诊,将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。必理通(对乙酰氨基酚片)是最风行的药物,在超市、便利店、药房都能买到。当地人伤风、发热、头痛城市来一颗。但我没有吃镇痛药的习惯,最后都是睡觉、喝水和期待自愈。